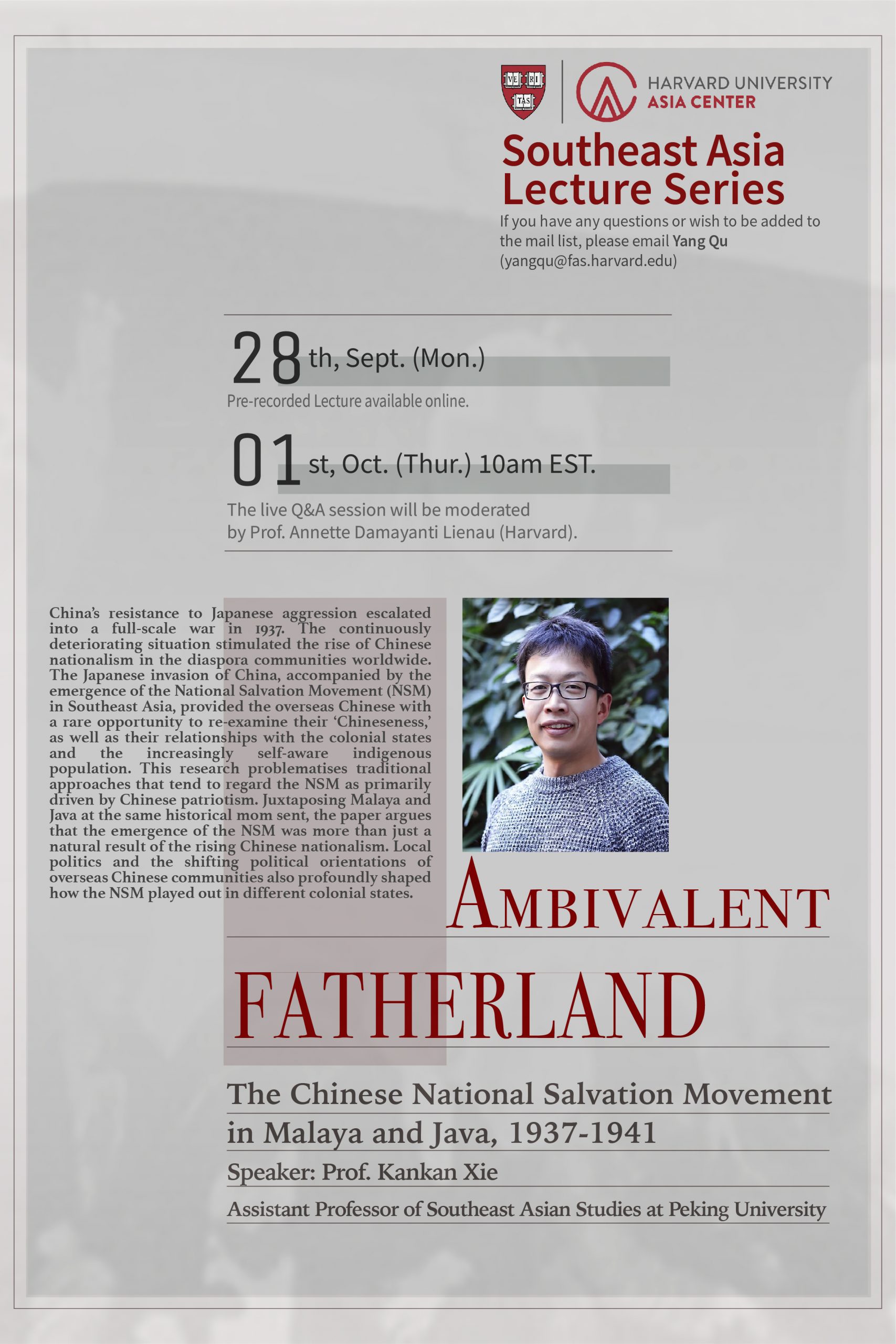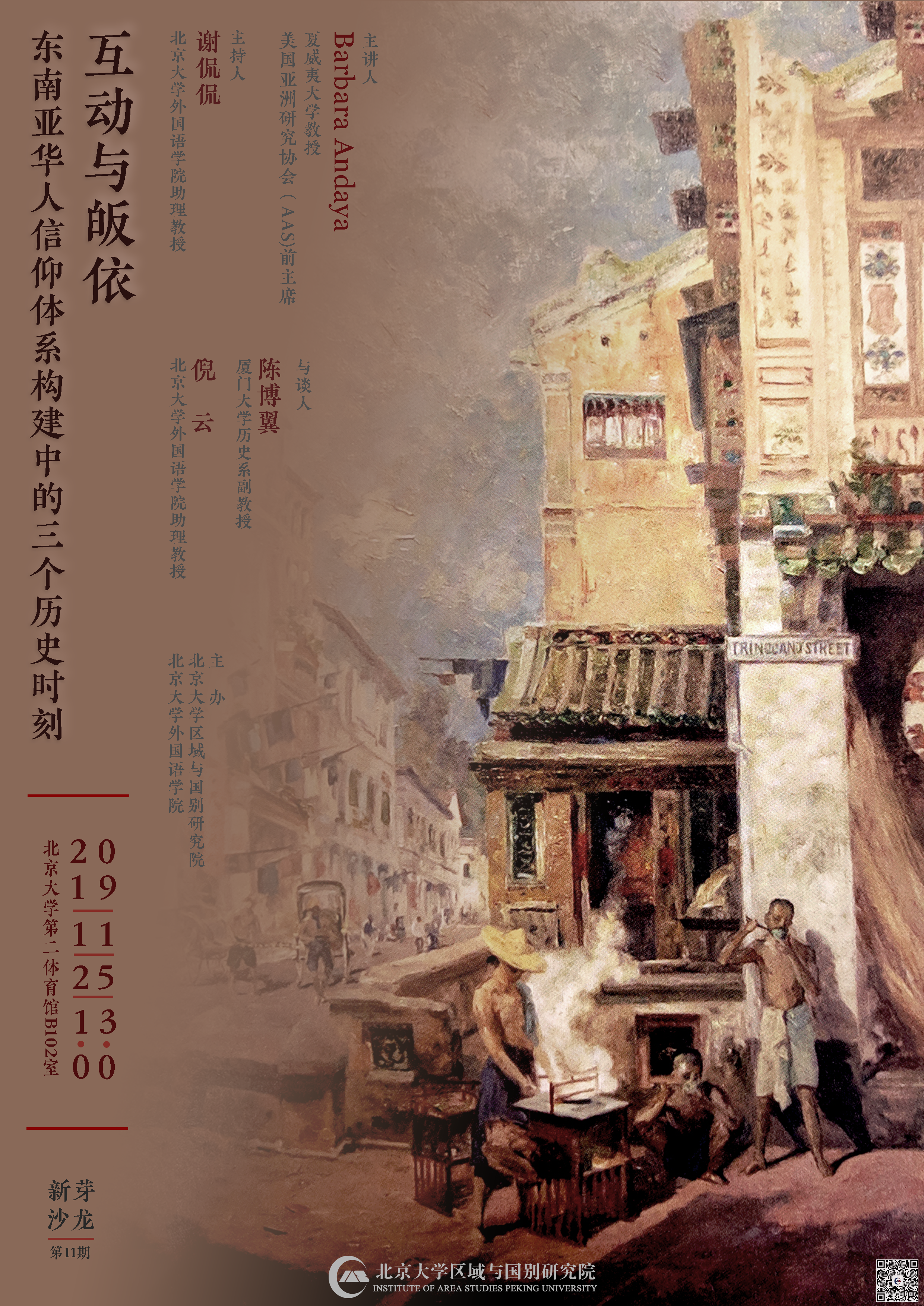|
07.
您所在的东南亚系是否有和北大校内其它院系或研究机构进行跨院系跨领域的合作研究?国内学界在东南亚研究领域的交流情况如何? 北大外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一方面,外院代表了北大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但200多名全职教师的体量却远大于国内综合性大学的外国语学院;另一方面,外院教师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历史、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宗教学等许多领域,可以说是一个自带跨学科属性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教学的集合体。外院东南亚系与院内许多系所都有合作关系,与原老东语系下的南亚系、阿语系、西亚系、亚非系等,以及新建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研究专业互动尤其频繁,合作研究和跨系开课都很平常。学校层面也有很多跨院系的合作平台,外院与历史学系和元培学院合办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与新闻与传播学院合办了“外国语言与国际传播”联合项目,也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亚太研究院、海洋研究院等跨学科平台与校内的国关、政管、法学、社会学、文史哲,甚至医学和理工科院系建立了合作关系。2018年成立的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进一步整合了校内区域国别研究相关学科的资源,跨学科对话及合作的机会是很多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杰克·M·福西(Jack M. Forcey)讲席教授T.J.彭佩尔(T.J. Pempel)有关东南亚发展型国家讲座
谢侃侃为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举行在线讲座,讨论马来亚和爪哇的中国民族救亡运动
08.
您在美国大学进行博士研究,另外还在荷兰还有东南亚当地都有过研究访学经历,您认为国内与美国、欧洲以及东南亚国家当地在东南亚以及马来群岛研究中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何不同? 任何地方的学术话语体系都受到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地迥异的学术环境当然也形塑了当地的东南亚研究。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受到冷战区域研究的影响,最初跟去殖民、民族国家构建、现代化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对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南亚研究已经有机地融入了美国的学术生态当中。东南亚不仅是美国社会科学理论天然的“实验室”,也为美国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格尔兹对地方性知识,安德森对民族主义,斯科特对无政府主义的论述等。当代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跟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移民,人权、种族、性别、宗教、环境、气候变化、后殖民主义等议题紧密挂钩,焕发出新的生机。欧洲的东南亚研究曾深受其东方学传统和殖民知识生产的影响,但由于其与美国学界及其内部的深度互动,近年来在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是相通甚至趋同的。在某种程度上,植根于殖民知识生产的“法国的印度支那研究”、“荷兰的印尼研究“、”西班牙的菲律宾研究“已经慢慢转变成为了具有现代学术关怀的”欧洲的东南研究“。东南亚国家在二战后纷纷取得独立,学者们对自己国家的去殖民、民族国家构建、族群政治、宗教等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另外,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学者也开始慢慢地将目光转向周边,或者突破民族国家边界去研究移民、环境、文化遗产、区域合作等问题。此外,东南亚国家的东南亚研究也深受欧美学界的影响,当地学界与欧美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过去,与西方学界紧密接轨的新加坡东南亚研究算是该地区的一个特例,但现在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机构已经在东南亚遍地开花。上面提到过,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深受政府需求、经济活动和大众消费的影响,近年来在体量上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的趋势。但总体来说,当前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所产出的成果中具有较强现实关怀的政策类研究占据主流,基于长时间田野调查,使用多语一手资料,具有高度理论原创性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
09.
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国内和国外学者交流互动情况如何?您认为在交流和互动中,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到了国外学界怎样的影响?反之国内学界对国外同研究领域是否有所影响? 在疫情之前,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学者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互动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中国学者外出访学、调研、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越来越多,不少中国学生赴欧美或东南亚高校学习深造。而且这种交流绝非只是单向进行的,有中国学者“走出去”,也有国外学者被“引进来”,互联网也让资料的易得性显著提升。但即便如此,个人认为在东南亚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和外界的交流还远不能用“频繁”来形容,新冠疫情的出现又为学术交流制造了更多新的困难。抛开疫情因素不谈,我认为阻碍中国东南亚研究学者与国外同行交流的因素有两点:一方面,中国东南亚研究有着独特的话语体系、语言偏好、问题意识和学术生态,这与中国学术界在整体上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内循环”能力的学术共同体,许多学者即使完全不去进行国际学术对话也可以在中文刊物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优先满足国内需求,从而在国内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而另一方面,相比人文社科中的很多领域,东南亚研究的国际化步伐又是相对滞后的。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来说,“走出去”和“引进来”早就成为了一种常态,但最热衷于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的学者大多研究中国问题,因为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他们为国际学术界贡献“中国视角”或“中国声音”。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教授(Barbara Watson Andaya)有关东南亚华人群体和基督教信仰的讲座
在芭芭拉·沃森·安达娅教授有关东南亚华人群体和基督教信仰的讲座之后进行的专题讨论。参与者有(从左至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Barbara Watson Andaya)(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系),倪云(北京大学英语系),陈博翼(厦门大学历史系)和谢侃侃(北京大学东南亚系)
10.
欧美学界目前开始出现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并且去殖民化的呼吁,而您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认为目前许多国内学者的研究取向则以中国为中心而忽视了对象国的视角,您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于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开展会有何影响?未来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欧美学界对去殖民的呼吁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已进行了很长时间,这样的做法是欧美学界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纠偏,从而不断发展、向前推进的重要驱动力。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去殖民紧密关联,却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半个多世纪以来,“殖民”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涵,国际东南亚研究学界也不断对自身进行着反思。总体来说,去殖民的努力确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仍然任重道远,因此还需要继续推进下去。类似地,中国东南亚研究学界并非没有对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自觉与反思,“南洋研究”向“东南亚研究”的转向已经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而且很多的学者也已经在各自的研究中越来越严肃地正视这个问题。但对于研究东南亚的中国学者来说,“去中国中心”并没有标准的解决之道,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达成。因为它既要求中国学者对西方学界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学习与借鉴,也要避免将自己的研究做成欧美学术传统的衍生品;既要强调对东南亚本地材料、方法、概念的创新性的吸收与使用,也要避免被本质主义支配;既要不断推动并深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互动,也有必要坚持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近年来,“内循环”与“外循环”是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高频词汇,对东南亚研究领域来说似乎也是适用的。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传统,丰富而特殊的学术关切,以及不断增长的学者、学生群体,使得该领域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地区东南亚研究的学术生态,具有很多地方所不存在的“内循环”基础。 凭借这一基础,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也保持活跃。但一味强调“内循环”也是有问题的,长此以往只会导致学者们闭门造车、思想僵化,知识生产停滞不前。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外循环”是亟待中国东南亚研究学界重启并深化的——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需要走向世界。
更多作者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反思可参见: Xie, Kankan. “Experienc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A Reverse Culture Shock.”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2, no. 2 (2021): 170–87. doi:10.1017/S0022463421000473 (责任编辑:) |